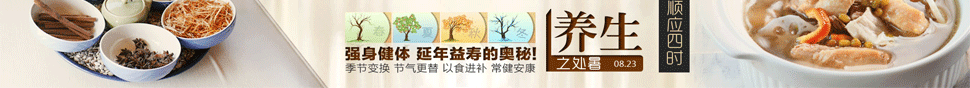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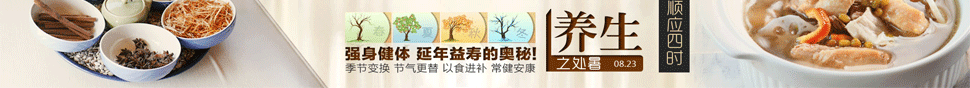
原标题:注目南原觅白鹿
陈忠实晚年时在家乡灞河畔。邢小利摄
年《白鹿原》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白鹿原北坡下的陈忠实旧居。邢小利摄
今年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年—年)80周年诞辰。陈忠实书写关中平原乡土社会变迁的鸿篇巨制《白鹿原》名列中国当代文学经典,而位于西安城郊的“白鹿原”也因此书而为世人所熟知。“白鹿原上有白鹿,世间已无陈忠实。”在陈忠实80周年诞辰之际,再上白鹿原,重温“白鹿原的陈忠实和陈忠实的白鹿原”。
壹
出西安城区往东,遇出自秦岭而北流的浐河。沿浐河往北,会自东西来的灞河。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称灞河为滋水,浐河为润河,滋润二水从东北西三面环绕一原,即白鹿原。白鹿原居高临下,西望长安。地质学认为,此原为亿万年形成的风成黄土台原。清代学者、陕西巡抚毕沅,在《关中胜迹图志》中考述白鹿原之得名,引《三秦记》说:“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原,以是得名。”
西周亡,东周初年,有人见到白鹿原上有白鹿。白鹿原上什么时候没有了白鹿,无从查考。至少从《白鹿原》所记述的清末以至于今,未见白鹿原上有白鹿的记载。
年夏天,陈忠实已经写完了《白鹿原》,他感慨万端,填了一首词《小重山·创作感怀》:
春来寒去复重重。掼下秃笔时,桃正红。独自掩卷默无声。却想哭,鼻涩泪不涌。
单是图名利?怎堪这四载,煎熬情。注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
陈忠实写完《白鹿原》,“注目南原觅白鹿”,结果是“似闻呦呦鸣”,但他没有看到白鹿。
年7月,一个黄昏,我驾车西上白鹿原,转从白鹿原北坡下去,就到了西蒋村。村边就是陈忠实旧居,陈忠实生前总是称这个地方为“祖居老屋”,现在这个“祖居老屋”的门前立着一个牌子:陈忠实旧居。我站在门外,绿树掩映之中,故居还是当年的样子,我熟悉的老样子。只是大门紧锁着。
这个被陈忠实称为“祖居老屋”、今天又被称为“陈忠实旧居”的院子,现在静静地隐在大树的浓荫之中。我知道,院子后面,就是白鹿原的北坡。北坡上某一处,是陈忠实的墓地。小小的一块地方。墓地朴素,有一棵松树,一块黑色墓碑,上面写着“陈忠实之墓”。
年春天,陈忠实住在西蒋村老宅,在为创作《白鹿原》做准备的阶段,他找乡亲们帮忙,在祖居老屋的地面上,亲手建成了一院新房。这新房或者说新院落,我来过很多次,不进去都很清楚:院子倚着白鹿原北坡,坐南朝北,面向北面的滔滔灞河。院子格局是:门楼,前面小院,前房三间,中间院落,种有小树花草,后房三间,后面小院,小院背后是白鹿原北坡,坡底下,当年凿有一个小窑洞,夏天可以在里边乘凉。年7月23日下午,就是在这个窑洞里,陈忠实与西安光中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安、总经理赵军谈成并签订了《白鹿原》电视剧改编版权的合同。
老家新房建成,陈忠实把后房三间中的右边的那一间,约有十多平方米,做了他的书房。这个书房,是陈忠实年底写完《白鹿原》、住回城里之前,他读书创作之所在,其中存放着他数十年间所购、所藏之书刊。这个书房共有三个两开门书柜,其中两个稍宽一些,样式一样,上边是花纹玻璃推拉门,里面分为三层,下边是木拉门;另一个较窄,上边是木框镶透明玻璃拉手门,里面分为四层,下边是木拉门。当年,我把陈忠实在这里的藏书全部拍了照片。他的藏书大致有一个归类,如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但总体上没有很细致地分类存放,看起来是散乱摆放的。从所藏书刊来看,书多,刊少。书主要是文学书,文学书里又多是外国文学作品。
前两年我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李建军等朋友还来看过这个书房,旧貌依然。前几天遇到西北大学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王鹏程先生,他说他近年有一次来看这个书房,偶然看到书房桌子抽屉里还散放着一些作家、学者给陈忠实的信件。看来,陈忠实的这个故居,特别是他的书房,还依旧样保存着。
新房建设时,陈忠实还在前房屋后廊沿两边的石子墙上,以深色石子各作了一幅画,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和海燕,算是山水画吧,镶在墙上。这是陈忠实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作画。
这就是现在的陈忠实故居。它是20世纪80年代陕西关中农村居家小院的典型风貌。当然,它也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属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的作家陈忠实的文化气息。
贰
依我的观察和了解,陈忠实的人生观总体上属于实用一类,他较少浪漫,不喜欢务虚。比如对于旅游,他并不热衷。但是,他专门去过三个作家的故居或者是家乡。
绍兴鲁迅故居,乌镇茅盾故居,湘西凤凰沈从文的墓地,陈忠实都去过。去,都是为了他心仪的作家。
年5月底至6月初,陈忠实应邀到浙江省金华市参加中国小说学会第五次年会。会后,他与李建军等人专程去了绍兴。在绍兴,他参观了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他说:“每个弄文学的人都应该到这里来归宗认祖。咱们这是来归宗认祖哩。”对于某些丑化或诋毁鲁迅的言论,他大惑不解,说:“这些人都不想想,把鲁迅都否定了,那现代文学史上还剩下啥东西不能否定?问题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谁达到鲁迅的高度,还没有谁像鲁迅那样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病根和问题挖得那么深。”可以看出,陈忠实对鲁迅的认识中,重视的是鲁迅对民族病根和问题的解剖。
年10月下旬,陈忠实参观了乌镇和在乌镇的茅盾故居,随后写了散文《在乌镇》。在这篇散文中,他深情地叙说:“一千余年的古镇或村寨,无论在中国的南方或北方,其实都不会引起太多的惊奇,就我生活的渭河平原,许多村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纪年之前,推想南方也是如此,这个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太悠久了。我从遥远的关中赶到这里来,显然不是纯粹观光一个江南古镇的风情,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之一的茅盾先生,出生并成长在这里。这个镇叫乌镇。乌镇的茅盾和茅盾的乌镇,就一样萦绕于我的情感世界,几十年了。”(陈忠实:《在乌镇》)陈忠实回忆他读高中时的情景:“游览在东溪河上,我的思绪里便时隐时浮着先生和他的作品。周六下午放学回家的路,我总是选择沿着灞河而上的宽阔的河堤,这儿连骑自行车的人也难碰到,可以放心地边走边读了。我在那一段时日里集中阅读茅盾,《子夜》《蚀》《腐蚀》《多角关系》,以及《林家铺子》等中短篇小说。那时候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教育主管部门在中学取消体育课的同时,也取消晚自习和各学科的作业,目的很单纯,保存学生因食物缺乏而有限的热量,说白了就是保命。我因此而获得了阅读小说的最好机遇。我已记不清因由和缘起,竟然在这段时日里把茅盾先生所出版的作品几乎全部通读了。躺在集体宿舍里读,隐蔽在灞河柳荫下读,周六回家沿着河堤一路读过去,作为一个偏爱着文学的中学生,没有任何企图去研究评价,浑然的感觉却是经久不泯的钦敬。四十余年后,我终于走到诞生这位巨匠的南方古镇来了,这镇叫乌镇。”
陈忠实写他参观茅盾故居的所见与所感,写得很细,表明他观察细微,想的也很多。他谈到茅盾乡土小说对他的影响,特别提到他在参观中“联想到我曾经在中学课本上学过的《春蚕》,文中那个因养蚕而破产的老通宝的痛苦脸色,至今依然存储在心底”,并且“意识到养蚕专业户老通宝的破灭和绝望”,并非茅盾在自家的深宅大院里体验感受到的,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是茅盾的“眼睛和心灵”“投注到”“无以计数的日趋凋敝的老通宝们的茅屋小院里去了”的结果。因此,“学习《春蚕》时的感觉,竟然没有因为老通宝是一个南方的蚕农而陌生而隔膜”,反而觉得“与我生活的关中地区的粮农棉农菜农在那个年代的遭际也没有什么不同”。陈忠实进而谈道,“这种感觉对我一直影响到现在”。因此,他后来“不大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beishacan.com/bsszy/11181.html


